“惡搞”文化泛濫凸顯網站編輯力之跛_網絡編輯教程
近兩年來,“惡搞”一詞充斥我們的眼球,甚至有一發不可收之勢。然而,“惡搞”在娛樂大眾的同時,也帶了諸多的弊端,部分“惡搞”作品甚至成了危害社會和諧的公害。然而,學者們在關注“惡搞”時更多的把眼光放在了“惡搞”本身的合理性和“惡搞”的法律依據等方面,對于“惡搞”流向社會的主要傳播途徑——網站編輯環節的研究卻少之又少,在眾多低劣“惡搞”作品的背后,也凸顯出網站編輯力的嚴重不足。
關鍵詞:惡搞 網站編輯 把關
近兩年來,“惡搞”一詞充斥我們的眼球,惡搞歌曲,惡搞明星,惡搞電影……就連我們平時同事之間開玩笑也會戲稱為“‘惡搞’了XX一下”,似乎世上的一切都與“惡搞”關聯。然而,“惡搞”在娛樂大眾的同時,也帶了諸多弊端,部分“惡搞”作品甚至成了公害,危害社會的和諧。然而,學者們在關注“惡搞”時更多的把眼光放在了“惡搞”本身的合理性和“惡搞”的法律依據等方面,對于“惡搞”流向社會的主要傳播途徑——網站編輯環節的研究卻少之又少,在眾多低劣“惡搞”作品的背后,也凸顯出我們網站編輯力的嚴重不足。
一、“惡搞”變“搞惡”,“惡搞”作品“越界”
現在很多學者認為“惡搞”一詞來源于日本的“kosu”,也有人認為“惡搞”就源于國內。我們且不論“惡搞”這個詞的的來源,僅對“惡搞”這個詞意思的理解就有不同的看法,大家普遍認為“搞”就是搞笑、搞怪的意思,分歧主要是對“惡”這個字的理解。一種認為這個“惡”字可以理解成程度很深的意思,是“搞”的限制語,類似的詞語還有“惡仗”、“惡斗”、“惡補”等,“惡搞”這個詞就可以理解成“狠狠地搞”、“猛搞”。在這里,“惡”是一個中性詞,“惡搞”這個詞也沒帶有什么貶義。另一種看法認為“惡搞”中的“惡”字等同于我們常說的“壞”字。在這里,“惡搞”就成了要把別人往壞處搞,要故意丑化別人的形像,有點嘩眾取寵的意思。很明顯,這里的“惡搞”帶有很強的貶義色彩。
而在現實生活中,“惡搞”也確實存在著兩面性,然而學者目前卻沒有對它們進行具體的定義,對于那種相對積極的“惡搞”,有些學者為了強調它們的創新性就尷尬地把它們稱作“善意的惡搞”,但隨著“惡搞”的風行,“惡搞”已不僅僅是前期的“滑稽模仿”“娛樂大眾”,而越來越呈現出“娛樂一切”的趨勢,“惡搞”的“惡”逐漸變得突出起來。“惡搞”的對象和方式逐漸“泛化”,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無孔不入,它在對事件或人物進行夸張放大的同時,更多的是故意去丑化某個形象,不顧時間和地點,不顧原有作品的完整性,對著名或眾所周知的人物、作品進行肆意改動,對名人、名作甚至是優秀的革命傳統進行惡意嘲諷。①現在有很多學者把周星馳的《大話西游》歸作中國“惡搞”的源頭,實際上,我們現在所稱的“惡搞”與《大話西游》采用的“戲仿”大不相同,“戲仿 ”是對于已有的文本、著作的一種模仿和創新。它所仿的對象不拘囿于已固定的文本形式,而是包括有文本的人物、對話、情節、結構、主題、意境等方面。新的文本往往只保留原作中的一些投影,二者差別一般都比較明顯:在經過“戲仿 ”后,新的文本往往成為一部獨立的作品。而且“戲仿 ”的本體大多選擇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文學作品,所以本體一般都不會出現。“戲仿 ”最常見的形式是沿用原作中著名的人物形象,但常會賦予新的時空背景和新的主題。‚而在我們所說的“惡搞”作品中,有很多以別人現有的作品作為素材,以胡戈的《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》為例,整個作品中的視頻部分完全采用電影《無極》和《中國法制報道》的畫面,這無疑是一種侵犯他人著作權的違法行為。還有部分“惡搞”作品,為了單純追求搞笑的效果,在創意上流于庸俗,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線,顛覆了原有文化中對精華的理解,淪為了“惡俗的搞笑 ”和“惡意的搞笑 ”。如對一些革命先烈的“惡搞”,對一些文化經典的“惡搞”等,在網上流行的一些“惡搞”作品,把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詞公然改編成了低俗的“黃色段子”,如在網上流行的對周杰倫的部分歌曲的改編等,不僅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權,更是公然傳播色情,這些都超越了我國法律的底線。類似“芙蓉姐姐”、“天仙妹妹”、“網絡小胖”等“惡搞”作品,雖然尚在法律的許可范圍之內,但他們以故意丑化自己嘩眾取寵的行為卻是與我們提倡健康、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觀相背。
二、網絡編輯把關不嚴也是“越界惡搞”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
在現有學術論文中普遍認為需要對“惡搞”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,以降低所謂“惡性‘惡搞’”的負面效應。如胡忠青在他的《“惡搞”紅色經典影片:跨越底線的顛覆與解構》一文中指出防止低劣“惡搞”的幾個對策:一是要積極引導網絡經營者傳播先進文化和文明辦網;二是要加強立法及網絡道德教育,加強道德自律,設置專門的管理機構,為互聯網內容管理立法等。ƒ耶丹在《論網絡惡搞現象及其控制》一文中也指出要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進行控制,短期的如加強政府管理、法律約束和技術控制等,長期的主要是要提高受眾的需求品味和媒介素養。④他們大多強調從傳者和接受者的角度進行分析,要求提高傳播者和接受者自身的素質,自覺傳播和接受健康的作品,抵制低俗的作品。由于過分的關注新媒介給受眾帶來的傳播權的擴大,而忽略了在傳統媒體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——編輯在控制“惡搞”泛濫中的重要作用。
近幾年,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使“眾人狂歡”的同時,也使人們過分陶醉于技術的發展,把話題主要集中在網絡給人們生活帶來的便利,突出平民話語權的獲得。一方面是網絡的飛速發展,確實給昔日的“草根”帶來了自我表達的機會;另一方面是網站編輯力的嚴重不足使網絡提供的“文本”難于適應社會發展潮流,甚至出現了一些對社會有害的負效應,如盜版泛濫、黃色文化流行等。
我國著名的編輯學家王振鐸先生曾經在他的《編輯學原理論》一書中提出了編輯的三大原理:文化締構原理、符號建模原理與訊息傳播原理。編輯也就是對信息進行選擇加工,并構建合適的媒體進行傳播,最終締構人類文化大廈的活動。這些作為編輯普遍規律的“原理”是一切編輯工作應該遵循的“道”,在網絡編輯工作中依然適用。但是網絡編輯的現狀卻不能令人滿意:由于過分強調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平民話語權的獲得,我們在不斷地構建新的傳播平臺,如“博客”、“互動雜志”等,這些平臺的構建使得我們進行信息交流的“帶寬”大大增加,人們似乎從來沒有能夠像現在這樣方便的溝通,然而網絡編輯在控制信息的流向方面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,也就是說我們過于強調符號建模而弱于訊息的傳播。我們說網絡弱于“訊息傳播”并不是從傳播的“量”的方面進行考察,網絡的大容量是其較傳統媒體的一個巨大優勢,它的弱主要是從傳播的“質”的角度來衡量,也就是網絡編輯對傳播內容的“把關”不夠嚴格,對傳播內容的質量控制不足。在“把關”作用沒有正常發揮的情況下,網絡編輯要發揮自身的積極作用,為構建和諧建康的文化添磚加瓦也就成了一句空談。
網絡編輯之所以沒有起到很好的“把關”作用,首先是網站編輯的素質普遍不高,網絡編輯人才嚴重短缺造成的。隨著網絡的迅速發展,我們的教育難以為網絡的發展提供足夠的人才,目前中國網絡編輯的總人數在300萬以上,然而受過正規教育的網絡編輯卻是鳳毛麟角,很多網站的網絡編輯只是從一些電腦職業學校畢業,還只有中等學歷,他們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技術層面的加工,對于文化產品內容的加工幾乎成為天方夜譚。在這種情況下,想要他們像傳統媒體編輯一樣去擔當“把關人”的角色似乎顯得有些勉強。在一些“惡搞”作品公然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線,有違社會和諧的時候,我們網絡編輯不但沒有及時地去“把關”,對它們泛濫進行控制,甚至還參與其中,給它們的傳播擔當了“舵手”。
網絡編輯沒能夠很好地“把關”,也與目前整個社會環境密不可分。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,互聯網似乎成了人們心中的神話,“技術主義論”已經有了抬頭的趨勢。普通民眾對于互聯網的認識不足,編輯活動“失范”現象不斷發生,在目前的編輯理論和相關法律不夠健全的情況下,網絡編輯的活動較傳統編輯顯得有些無所適從。民眾的法律意識不強,只沉醉于在互聯網上集體“狂歡”,公然不顧他人利益,一部分網民成了沒有任何社會責任感的“烏合之眾”。在胡戈的“惡搞”作品侵害別人合法權益的時候,我們的網民不是站在受到侵害的一方,而是為侵權者吶喊助威,給被害人的訴訟制造壓力,這無疑又是一次更為深刻的“惡搞”。
總之,為了防止“惡搞”變“搞惡”,我們要對“惡搞”進行合理的引導,發揮其正面作用,遏制其負面效應。在這個過程中,我們的網絡編輯曾經顯得無力,但我們的網絡編輯應該而且能夠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。作為網絡編輯承擔的責任很大,網絡傳播的匿名性 、復雜性 、亟待規范等特點都給網絡編輯的“把關人”角色添加了更多的責任。面對紛繁復雜的局面,網絡編輯要有嚴肅的態度,擔當起自己應負的責任,杜絕虛假信息及色情、暴力等不良內容,保證我們的網絡一路走好。
- 相關鏈接:
- 教程說明:
網絡編輯教程-“惡搞”文化泛濫凸顯網站編輯力之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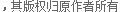 。
。